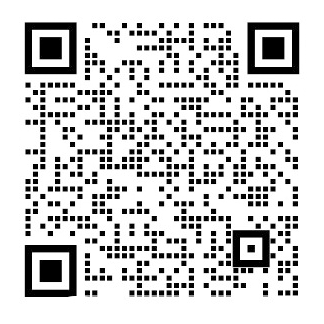俄国东正教在华传教效果研究
1715-1956年间,共有20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被派往中国,早期俄国传教士团成员有固定的编制,受到中俄两国官方的认可,并享受政府的薪金补贴。以服务在华俄国后裔的宗教生活为主要任务,并带有外交政治职能。其传教效果甚微。1861年至1917年,中国同意其在华传教,相对而言,传教环境有所好转,并由于俄国驻华外交馆成立,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的重要性减弱,此时,东正教传教士团的传教效果有所改善。1917年,俄侨的涌入,使得东正教规模迅速扩大。以具有地理优势的哈尔滨教区为例,首先,神职人员数量增多,使得东正教有能力服务更多的教徒,其次,俄侨多为东正教信仰者,在华教徒数量而随之增加。一直到1956年,虽在华东正教会拥有自主权,在华俄桥人数也大幅度萎缩,并至文革前期,中国东正教几乎不复存在。
一、早期的俄国传教活动
自清朝开始,在中国北部毗邻俄国西伯利亚的交界地带,两国边民常常发生纠纷,康熙为平息骚扰,三次派兵攻打阿尔巴律地区,并把这些战俘相继地送往北京编入八旗兵镶黄旗中,供给官职、房屋和土地。康熙为尊重俄国战俘的宗教信仰,“还将胡家园胡家内的一座关帝庙拨给他们作为临时祈祷所。”[1]并由战俘马克西姆bull;列昂节夫神父主持日常宗教工作。俄国东正教最初就是由这些战俘传入中国的。而康熙皇帝的宗教宽容政策为东正教在中国的立足提供了必要条件。俄国战俘在中国受到优待并被允许保留东正教信仰的消息传入俄国政府后,彼得大帝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于1700年下达谕旨[2]命基辅都主教选择一位善良、饱学和品行端正的人前往离中国最近的托博尔斯克地区担任主教管理在华东正教传教工作相关事宜。并多次向清政府提出向北京派遣神父的要求。1711年,马克西姆bull;列昂节夫神父在北京去世,俄国商务专员胡佳科夫按照彼得一世的旨意,提出希望中国方面准许俄国派遣修士大司祭来北京接替马克西姆bull;列昂节夫司祭的神职工作,并以此作为俄国方面同意清廷大臣殷扎纳等人经俄国境内访问流落的蒙古部落及其首领阿玉奇的交换条件。[3]清政府同意后,俄国向中国派遣了第一届传教团。又根据1727年《恰克图条约》俄国所取得的定期派遣传道团到中国的权利,此后到1858年,共有十三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团被派遣到中国。
早期俄国东正教在华传教服务对象主要是俄俘,俄国馆仆人和少数穷人。虽然俄国东正教一开始就以服务俄国侨民的宗教生活为目的出现在中国,但从记载的资料来看,早期在雅克萨战争中被俘而送往北京的俄国战俘在长期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之下大多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正教信仰。“这些阿尔巴律人,除其中三人(此时应该说已是几户)外,其他人从在北京定居之日起就对基督教毫无诚意。”[4]尽管如此,经过驻北京传教团的努力,也曾让一些阿尔巴律人的后代重新受洗。例如“第五届传教团在京期间,通过阿尔巴律人受洗翻译对未受洗阿尔巴律人进行训诫和教诲,让50名阿尔巴律后代全都受了洗。”[5]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在俄馆的仆役和少数穷人因为受洗可以拿到银制十字架和少许衣服和银两外,很少有受洗者。“中国人很少去教堂,只有一些仆役乐意来俄人教堂,摘了帽子站在门口听祈祷。”[6]而对于这些因为能通过信仰东正教而有所受惠才选择信仰的人来说,其信仰意志是薄弱的。常常出现一些仆役一旦不在俄国馆做事之后或者教堂因自身财力有限无法再为部分穷人提供小惠的时候,他们就不再信仰东正教的情况。据第八届传教团大司祭尼bull;伊bull;维谢洛夫斯基回忆“俄国人只要一把自己领洗过的仆役辞退,那么,这个仆役除咒骂、污蔑自己过去的主人外,以后就再也不上教堂了。”[7]在受洗的人群中,还有一类更为短暂性的信仰者,他们多以自身具体利益为准。例如在俄国商队来北京期间,有部分人为了能较为方便地同俄国人做生意而受洗,但在商队离开之后,便不再进入教堂。
与同一时期西方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教的情况相比,俄国东正教虽然自1715年第一届传教团来华之后一直未遭到清政府严格意义上的打压和驱逐,但其传教效果甚微。究其原因,可以从其目的、宗教背景和传教教会自身情况几个方面看出一二。
首先,早期来华的东正教传道团是在中国不允许外国在本国设立外交机构的情况下,作为俄国在中国的集宗教、外交和商贸为一体的战略据点而存在和受到重视的,同时其日常活动也以服务在华俄侨的宗教生活为主。虽然其派遣机构有向中国传播东正教的想法,但一直没有将其作为在华传道团的主要目的。到1818年,沙俄政府甚至明确指示在华传教士团:“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迸行全面研究,井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8]自此到1861年,驻北京传道团专注于关于中国事态的情报收集工作,这些资料受到俄国政府的重视,成为俄国胁迫中国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重要的一环。以第十三届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巴拉第为例,他在写给《瑷珲条约》全权负责人穆拉维约夫的报告中提出了大量建议,“中国政府由于内乱四起,不得不对于我国采取妥协政策。”“此间政府对有争议的黑龙江一线既明知难保,势必承认新边界这个事实。”[9]使得穆拉维约夫作出了更有利于俄国的决策。
其次,早期东正教在华传道团内部纪律松散,教会成员素质普遍不是很高。东正教在华传道团的宗教成员一般由一名修士大司祭、两名修士司祭、一名修士辅祭和两名教堂辅助组成。领班传教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常常会写到自己属下人员不听管教顶撞自己甚至恶意攻击自己的情况,被派往北京的传道团一般在北京待十年,但其任期时间并无定制。他们这种为所欲为,不受管制的行为主要归结于以下两点:一则他们会在北京呆很长的时间,天高皇帝远,基本受不到俄国本土的制约;二则一般回到俄国他们也不会因为这种行为受到任何惩罚。既然教堂人员基本没有什么规则顾虑,这些人很难去维持一个良好的教堂秩序。“不仅修士司祭可以随随便便当着那里居民的面极其下流无耻地指着鼻子辱骂自己的上司修士大司祭,连教堂辅助人员和学生也都可以轻易地干出这种事来。”[10]这也导致当时本身优越感强的中国人对俄国东正教很没好感。“说它既不教其信徒遵守教规,也不教他们遵守良好秩序,所以俄国人没大没小,每个人都妄自尊大。”[11]除此之外,还常常出现教会人士过度纵酒而命丧黄泉的现象,在早期派往北京的十三届传道团中,有七届传教团团长因饮酒过度等原因导致身体状况太差最后在北京去世。俄国人自身具有饮酒的习惯,加上北京更为湿热的气候,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容易使身体受损,再者,因为远离家乡而带来的归宿感的缺乏,又使得他们借酒消愁,常常处于消极怠工的状态。
在传教方式上,俄国东正教在华传教过程中一直未完成相应的中国化过程。十六世纪末,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过程中,曾先后打扮成和尚和儒士以便被中国人接受,并利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试图拉拢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统治阶级,还配以当时而言相当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其核心在于包装中西文化,使得出现交融的局面,而使得中国人更容易去接受天主教所信奉的教义。相对于此,俄国在华东正教却一直保留着东正教自身的习惯。从最高圣务会给传教团的训令中可以看到,“不得添加任何迷信的东西,毫无意义的故事,伪造神的奇迹和启示,尤其不得自己杜撰一套,以免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12]在早期历届传道团中,很难看到有人将东正教教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进行传教的。在其穿着相貌上,当时在华的俄国人依然蓄着大胡子,穿着高筒帽子和窄腰肥袖的袍子,和中国人完全不同,也使得中国人心理上认为他们是野蛮之辈,更不屑于以他们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