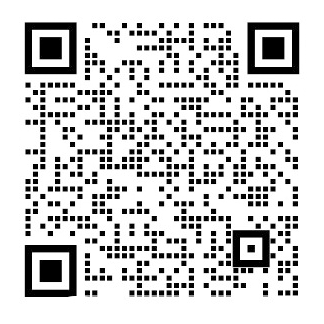|
|
||||||||||||||||||||||||||||
|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居住理念也在不断更新。当代的居民,已普遍将良好的居住环境视为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也越来越重视居住环境的污染问题。在选择住房时,居民往往会考虑其周边是否存在化工厂、发电厂等环境污染源,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居住选址的决定。所以,在同一住房市场范围内,由于住房所处区域环境污染源的分布情况不同,其住房价值也会有所差别。 居住环境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更是对生活质量优劣进行评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尺。随着城市居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人们渐渐意识到良好的居住环境对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居民在选择自己的住房时也会尽可能远离那些对环境与健康有负面影响的企业。 对于居住选址,城市居民的普遍选择都是环境宜人、无空气和水土污染、无噪音、无恶臭并且视觉良好的地区;对于那些易对周边环境产生污染的企业,人们则不愿意居住在其附近。在我国,将会对其周边环境产生负外部性而易遭到公众抵制的公共设施称为“邻避设施”,本研究专门针对的是“邻避设施”中的环境污染源这一类。 本文献综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环境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对于附近居民健康与居住环境的危害;第二部分介绍污染性企业的开放对于周边住房价值的影响;第三部分在对目前所做的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说明本研究的意义所在,并探讨接下来的研究方向。 1 各类污染源对居住环境的影响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研究重点放在污染密集型企业对于居住环境污染状况上,通过整合这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总结了这类研究主要针对六种污染源:火力发电厂、钢铁厂、化工厂、水泥厂、造纸厂、垃圾填埋厂。这六种污染源会通过排放各种环境污染物,从而对其周边的水环境、大气环境和土壤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笔者将其通过表格进行表示: 1.1 火力发电厂 近些年来,中国居民的用电量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这使得火力发电厂的数量也逐年递增。尽管目前已出现清洁能源用于产生电能,但如今绝大多数的发电厂仍是采用燃烧化石燃料进行发电,这就使得其在运行过程中,对环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效应。Davis(2011)就提出,建设新发电厂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选址时其周边居民的反对,他指出对于居住在发电厂附近的居民来说,发电厂的运行会伴随一系列负外部性的产生[1]。 在所有负外部性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火力发电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传统火力发电厂在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对大气构成直接危害的主要污染物有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2]。Srivastava等人(2004)也提出,火力发电过程中会向空气中排放过量的三氧化硫,导致大气能见度降低和酸沉降(酸雨)[3],Srivastava等人经实验测定发现目前三氧化硫排放超标问题是目前大多数火电厂的“通病”;另外,火力发电时使用的粉煤灰的“磁性组分”中富含铬、锰、钴、镍、锌等重金属[4],在煤炭的燃烧过程中,这些重金属微粒也会聚集起来并随着火电厂的烟囱排放到大气中并使水源和土壤发生重金属污染[5]。 我国的研究侧重于对污染物的监测。张伟(2014)提出,火电厂产生的对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污染物主要有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6];周武元(2016)提出火力发电厂对环境的污染除大气污染外还有热污染,热污染对于火电厂附近居住环境的气候存在一定影响[7]。此外,张育兰(2000)提出,火电厂排放的废水中包括油污水、煤场排水、地面冲洗水,并且水中还含有重金属,这会污染火电厂周边的水环境[8]。 1.2 钢铁厂 由于钢铁厂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以及噪声都会对居民的居住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近些年地方政府也高度重视钢铁厂的选址问题。 Lorenzo Liberti等人(2006)对于意大利一处合资钢铁厂的炼焦炉组进行持续监测,结果发现其排放的多环芳香烃浓度远高于排放限值,而且他们还证明了这种有机污染物的过度排放是PM2.5浓度上升的重要原因[9]。Olmez(2015)和Dorota(2013)都是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钢铁厂的环境影响。Dorota提出,在钢铁厂的全寿命周期中,对环境影响最为显著的是高炉燃烧焦炭的过程和烧结厂冶炼铁矿石的过程,这些过程不仅使得能源大量消耗,也会造成温室气体大量排放以及重金属污染等严峻问题[10];Olmez认为,在热轧和钢液生产过程中释放的大量无机污染物不仅易使人患上呼吸道疾病,也会导致温室效应[11]。 国内方面,早在1993年,上海医科大学宋伟民等人就研究了钢铁厂氟污染对环境及儿童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钢铁厂周边土壤中的氟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地方,并且居住在钢铁厂周边的儿童氟斑牙等疾病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12];耿婷婷等人(2011)的调查结果显示,钢铁厂会带来大量的重金属污染,其进入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可迁移、转化和积累,从而对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造成危害[13]。 1.3 化工厂 目前,化工厂几乎已成为污染的代名词,由于设备泄漏等原因,化工厂往往是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直接污染源,这也造成居住在化工厂附近的居民存在着很大的患病隐患。 早在1981年,Wallace等人就通过动物的实验得出结论:即使化工厂排放出的有机物浓度很低,也会有很大概率诱发细胞癌变。Jin Kyu Kim等人(2003)更是提出,化工厂释放出的挥发性有机混合物易导致染色体断裂,并对人体有着严重的遗传毒性[14]。Donato(2005)通过实验发现,化工厂运作过程中会释放过量的多氯联苯,多氯联苯会通过食物(尤其是植物类食物)进入化工厂附近居民体内,导致癌症的发生[15]。Barry等人(2013)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上述论断,他们搜集了一个化工厂附近村民中患癌症的人数,这也是国际上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论证化工厂是否对周边居民患癌情况产生影响,结果显示居民是否患癌和他们血清中的全氟辛酸浓度显著相关,而排放全氟辛酸的“罪魁祸首”就是化工厂[16]。 国内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化工厂的潜在风险,比如刘元海(2007)结合哈尔滨市某化工厂生产与贮存氯气的实际情况,对其一旦发生突发性事故泄漏造成的风险区域的确定进行了研究[17];张建平(2016)提出,对于化工厂, 在进行储存运输原料实际过程中, 尤其是在管道处, 经常出现泄漏,这一方面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并对附近居民的健康安全构成威胁[18]。 1.4 水泥厂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对水泥企业污染源概念有关问题的复函》中指出:水泥企业达标后仍然会有污染物排放,其中不仅有水泥的粉尘排放,同时可能有其他的污染物,如煤炭燃烧释放的SO2、烟尘等,这些污染物的长期排放(包括长期达标排放)及其累积效应对周围的环境仍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 早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就普遍认为,水泥厂排放物会导致其附近居民咳嗽、痰多、呼吸急促等肺部疾病,进而会影响居民的居住选址[19]。Rovira等人(2014)搜集了巴塞罗那一处水泥厂附近的空气、土壤、植被的样本,测定这些样本的多环芳香烃、重金属等污染物浓度以研究水泥厂对于附近的居住环境的污染程度[20];另一方面,Laura(2016)研究发现,化工厂会对其周边土壤造成严重的重金属污染,重金属尤其是Hg的含量会远远超过对照组,这会大大降低土壤功效并造成农作物减产,重金属污染物还会对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21]。 国内方面,卿华(2016)提出,水泥厂主要大气污染物包括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水泥厂废气在非正常排放条件下,会使污染物浓度大幅度增加,对周围居住环境造成严重影响[22];赵文凯(2009)分析了水泥厂全寿命周期的环境影响,他提出水泥厂不仅会产生噪声污染,也会造成附近的水环境和大气环境质量下降[23]。 1.5 造纸厂 造纸厂在运作过程中,会排放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等大气污染物进入到空气中,对居住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MMirabelli和Wing(2006)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上述空气污染物易使居民患上哮喘等呼吸道疾病[24];另外,Susana等人的调查研究显示,由于造纸厂经常会产生砷、多环芳香烃等有毒物质,使得靠近造纸厂的居民区内的居民更易产生肺癌等癌症。 刘耀东(2015)提出,在造纸过程中,产生大量具有高毒性、持久性的化学污染物,容易在人类及生物体内堆积,造成人体内分泌紊乱,诱发癌症、神经系统等疾病的发生,进而威胁人类身体健康;另一方面,造纸厂排放的空气污染物危害人类身体健康,导致人类患有呼吸道疾病,并影响气候环境,既增加城市人口佝偻病的发病几率,又会引起温室效应[25]。 1.6 垃圾填埋场 对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处理, 无论是采用焚烧法、堆肥法、卫生填埋法,还是土地填埋法,都会或多或少地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而其中,又尤以土地填埋法的负面影响最为严重[26]。 基于2007年在西班牙发起的一个环境监测项目,Joaquim Rovira等人(2015)又测定了垃圾填埋场附近土壤和空气中的重金属浓度和二噁英浓度。结果发现,垃圾填埋场附近的重金属和二噁英浓度明显超标,这对于附近居民的健康存在着很大的负面影响[27]。 Palmiotto等人(2014)通过对垃圾填埋场排放的危险物质和恶臭进行风险评估,证明了垃圾填埋场附近居民出现的健康问题大多来源于垃圾填埋场排放的有毒气体;此外,在垃圾处理与填埋过程中,会产生严重的恶臭,Palmiotto等人经过实证研究发现这导致附近大量居民搬迁[28]。 国内对于垃圾填埋场的研究主要针对于其产生的垃圾渗滤液和填埋废气。赵勇胜等人(2007)对我国城市垃圾填埋造成的土地、地下水污染现状进行了3个实例分析,提出了垃圾渗滤液是造成填埋场附近土地和地下水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29];蒋满元和唐玉斌(2006)提出,垃圾填埋场在其漫长的稳定化过程中会产生的大量的填埋气体及其垃圾渗滤液,导致其在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内持续地对附近的公众健康和环境(如造成水资源污染、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植被破坏、影响周边景观、火灾、爆炸及填埋场本身的沉降等)构成严重威胁[26]。 2 污染对房价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研究污染企业对于周边环境和居民的影响,比如Kennth和Grennstone(2003)就通过研究发现,空气中TSP浓度每升高1%,就会使婴儿死亡率上升0.35%[43]。 因此一些学者希望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探寻污染企业对于住房价值的影响。在此之前,我先简要介绍一下特征价格法。 2.1 特征价格法 特征价格法,又称Hedonic模型法和效用估价法,认为房地产由众多不同的特征组成,而房地产价格是由所有特征带给人们的效用决定的。 郑思齐(2003)认为,特征价格法应当成为未来我国住房价格指数编制的主要方法[41]。在目前关于房地产价值的实证研究方法上,大量研究是通过特征价格模型进行的。吴璟等人(2007)还详细阐述了特征价格法的四种主要应用形式的基本原理及其优缺点和适用性[42]。 国外更是有大量运用了特征价格模型进行的研究,笔者将其以表格形式整理如下:
经过梳理,笔者发现这类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重点研究环境污染物对于住房价值的影响,二是研究污染企业的开放对于住房价值的影响。 2.2 污染物对于房价的影响 随着房地产的蓬勃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仅对房屋的质量要求提高,对居住环境也给予同样的重视。环境污染会对房地产的价值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里的环境是指大气、土壤、水等自然环境[30]。 Siqi Zheng等人(2014)证明了跨境的污染流对于当地的住房价格有着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城市周边流入该城市内部的污染物浓度每下降10%,将会使住房价格上升0.76%,而且跨境的污染流在较富裕城市产生的边际价值要明显高于较贫穷城市[44]。 Ardeshiri等人(2016)提出,由于目前没有很好的方法用以估计环境因素对人体健康带来的影响,所以有很多学者都通过房价变化来表征环境因素的外部效应。作者选取了伊朗某城市,搜集了400家刚刚做出居住选择的居民的数据,运用特征价格法和生活满意度指数研究环境对住房支付意愿和住房价值的影响。经过实证分析,对于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人们的支付意愿显著下降,因此住房价值也普遍较低[31]。 Jim和Chen(2016)的研究同样是基于上述思想,他们基于特征价格的线性模型和半对数模型研究城市环境因素对住房交易价格造成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衡量环境所带来的外部效应。该研究搜集了广州652个住房交易数据,并按照房屋属性将这些住房分类。结果显示:位于绿色区域或者靠近清洁水体的住房价格要比污染严重地区高7.1%—13.2%[32]。 Bayer等人(2009)运用特征价格模型研究空气质量对于居民居住选择的影响。为了控制经济活动、工厂运作等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地区空气质量差异,该模型排除了工厂排放等因素带来的影响。根据特征价格模型的估计,支付意愿关于空气质量的弹性为0.34—0.42,这意味着居住环境中的PM2.5等颗粒物浓度每降低一个单位,就会使每平方米支付意愿上升约149—185美元[33]。 Siqi Zheng等人(2009)还研究了住房价格、FDI流量和空气质量之间的关系,该研究选择使用跨城市的面板数据组,数据来源为中国的35个主要城市。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等级较高的城市住房价格普遍较低,而人均FDI流量较高的城市往往处于较低的环境污染等级[45]。 Lang(2015)调查了美国某地住房市场数据和环境质量空间分布数据,用以研究在1990年空气改善行动后住房价值和居民居住选择偏好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作者发现,空气质量改善的地区,住房交易价格会立刻显著上升,而房屋租赁价格略为滞后,但同样保持上升趋势[34]。 2.3 污染源的开放对于房价的影响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污染企业对于其附近的环境有着诸多不利影响,并且已有文献证实了居住环境的污染会对房价会产生负面效应,所以一些学者希望将这二者整合起来,研究污染企业的开放对于住房价值的影响。 周春晓(2014)提出,一旦某区建了垃圾处理厂、焚烧厂、核电站等邻避设施,其周围的房价必然会随之下降。一方面,经济实力丰厚的居民想主动避免邻避设施所带来的房产贬值、舒适度下降等负外部性影响,于是陆续迁出此地方;另一方面,房价的下降会吸引更多的低收入者迁入此地,进而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35]。 Davis(2011)选取了1993年—2000年新开放的92家发电厂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运用eGrid数据获取了发电厂的位置信息,随后Davis又搜集了在这些发电厂两英里范围内的住房数据(包括房价、租金等)和人口特征。作者以住房价值为被解释变量,以住房是否位于发电厂两英里范围内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建模,并得出结果:在发电厂附近两英里范围内,住房价值(房价和租金)平均下降4%—7%;此外,作者还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在发电厂附近,居民的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之其他地区都显著下降[1]。 Currie等人(2015)研究了排放有毒气体的工厂的开放和关闭对于住房价值的影响。作者首先测量了有毒气体排放的空气质量影响范围,他们选择了八个最主要的污染物进行监测并绘制浓度—距离图像,图像显示几乎所有污染物都以类似于指数的形式进行变化,大致在一英里处时,所有污染物浓度都趋向于0;然后作者搜集了TRI清单数据,并准确识别了TRI清单中所报道的工厂的位置;运用双重差分法估计距离工厂“较近”的地方和距离工厂稍稍有点远的住房价值。经过实证研究,作者得出结论:排放有毒气体的工厂的开放会使其周围0.5英里内的住房价值下降约百分之11,而工厂的关闭对于住房价值大体上没有什么影响[36]。 Katossky(2014)同样研究了排放毒害气体工厂对于房价的影响。作者选择了法国的三个重要城市,这三个城市的化工厂附近都居住着很多居民。作者以特征价格关于住房到化工厂之间的距离建立模型,估计化工厂对于房价的影响。尽管三个城市估计出的影响数值有很大差异,但三个结果均显著为负且影响程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小[37]。 Hanna(2007)研究了污染企业的开放对于其附近经济特征,尤其是住房价格的影响。作者搜集了TRI清单数据和1980年普查数据,在控制了截面偏差和时间偏差的基础上,估计随着距离的变化污染企业对于房价的变化。结果显示:住房离污染企业的距离每减少1英里,房价就会下降约1.9%[38]。 Greenstone和Gallagher(2008)的研究针对的是有害废物站点所带来的影响。该研究同样运用了特征价格模型方法,通过比较得到有效清理的垃圾站点与未得到有效清理的垃圾站点附近住房价格的差异,研究有害废物站点对于住房价值的影响程度。与期待得到的结果相反,有害废物站点的清理并未给其附近住房价值带来实质性的提升。作者认为,住房价值之所以未得到提升,在于有害废物站点为完全撤离,由于观感上的不适,人们对于其附近的住房的支付意愿仍然不高[31]。这也和Currie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工厂的关闭大体上不会对住房价值的上升产生贡献)相契合[39]。 陈佛保和郝前进(2013)以垃圾中转站为例,通过上海25197户二手住房价格的空间差异研究了城市居民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环境市政设施的支付意愿。研究结果显示,住宅到垃圾中转站的距离每减小1千米,住宅价格降低3.6%,表明居民对于垃圾中转站具有较强的邻避效应;垃圾中转站规模越大,其影响的范围越大,居民的邻避效应越强[40]。 3 国内外研究评述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关于居住环境污染源对住房价值影响的研究正由微观向宏观发展,微观层面的研究指的是污染物对于房价的影响,宏观层面的研究指是产生污染物的工厂、毒地等污染源对于房价的影响。对于国内的研究来说,目前绝大多数还都只是研究环境污染物的浓度对于住房市场的影响,针对污染企业的研究较少且都偏向于研究“邻避效应”下居民补偿意愿,并未真正涉及污染性企业对周边住房价值的研究;而国外关于污染企业对房价影响的文献,都是分析单一工厂对于周边住宅市场的影响,即先分析某污染密集型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范围,再分析这一范围内的住房价格在该企业建立前后的变动情况,但如果某住房同时位于化工厂、钢铁厂等多种邻避设施附近,其环境风险则不可能只针对一个企业进行计算,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针对单一污染密集型企业研究得出的结果就会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 所以这也是本研究的创新所在,即在运用ArcGIS软件建立污染源和新房项目图层的基础上,分析各个污染源的污染排放对各新房项目成交价格的影响。运用软件计算特征价格模型中所需要的变量,并构建多种污染指标,从而对各污染指标的影响系数进行估计。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更加契合实际情况,且较之研究单一企业对居民和房地产开发商更具有借鉴价值。 |
||||||||||||||||||||||||||||
|
参考文献: [1] Lucas W. Davis. THE EFFECT OF POWER PLANTS ON LOCAL HOUSING VALUES AND RENT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04): 1391-1042. [2] 石晓亮, 钱公望. 燃煤火力发电厂大气污染及其控制[J]. 污染防治技术, 2004(01): 97-100. [3] R.K. Srivastava, C.A. Miller, C. Erickson, R. Jambhekar. Emissions of Sulfur Trioxide from Coal-Fired Power Plants[J]. Air amp;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04(06): 750-762. [4] Hansen LD, Silberman D, Fisher GL. Crystalline components of stack-collected, size-fractionated coal fly ash[J]. Environ Sci Technol, 1981(05): 1057-1062. [5] Vassilev S. Phase mineralogy studies of solid waste products from coal burning at some Bulgarian thermoelectric power plants[J]. Fuel, 1992(7): 625-633. [6] 张伟. 火力发电厂大气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与控制措施[J].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16(24): 132-133. [7] 周武元. 浅谈火力发电厂的污染治理[J]. 科技展望, 2016(06): 151. [8] 张育兰. 火力发电厂与水环境[J]. 湖南电力, 2000(04): 53-54. [9] Lorenzo Liberti, Michele Notarnicola, Roberto Primerano. Air Pollution from a Large Steel Factory: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 Emissions from Coke-Oven Batteries[J]. Air amp; Waste Manage, 2006(03): 255-260. [10] Dorota Burchart-Korol.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steel production in Poland: a case study[J]. Cleaner Production, 2013(04): 235-243. [11] Gulnur Maden Olmez, Filiz B. Dilek, Tanju Karanfil, Ulku Yetis.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 life cycle assessment study[J]. Cleaner Production, 2015(09): 195-201. [12] 宋伟民, 卢纯惠, 李锦梅, 郑世军. 钢铁厂氟污染对环境及儿童健康影响的研究[J]. 中国公共卫生, 1993(03): 99-100. [13] 耿婷婷, 张敏, 蔡五田. 北方某钢铁厂部分厂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初步调查[J].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1(06): 343-346. [14] Jin Kyu Kim, Hae Shik Shin, Jae-Hawn Lee, Jeong-Joo Lee, Jin-Hong Lee. Genotoxic effects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a chemical factory as evaluated by the Tradescantia micronucleus assay and by chemical analysis[J]. Mutation Research, 2003(07): 55-61. [15] Francesco Donato, Michele Magoni, Roberto Bergonzi, Carmelo Scarcella, Anna Indelicato, Sergio Carasi, Pietro Apostoli. Exposure to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in residents near a chemical factory in Italy: The food chain as main source of contamination[J]. Mutation Research, 2005(11): 1562-1572. [16] Vaughn Barry, Andrea Winquist, Kyle Steenland. 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 Exposures and Incident Cancers among Adults Living Near a Chemical Plant[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13(11): 1313-1318. [17] 刘元海. 某化工厂液氯突发性泄漏风险的研究[J]. 环境科学与管理, 2007(08) : 65-68. [18] 张建平. 泄漏检测在化工厂运输管道的应用探析[J]. 技术管理, 2016(03) : 158-159. [19] Hyun Seung Lee, Chul Gab Lee, Dong Hun Kim, Han Soo Song, Min Soo Jung. Emphysema prevalence related air pollution caused by a cement plant[J]. Annals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2016(10): 1-8. [20] Joaquim Rovira, Jordi Flores, Marta Schuhmacher, Marti Nadal. Long-Term Environmental Surveillance and Health Risks of Metals and PCDD/Fs Around a Cement Plant in Catalonia, Spain[J]. Huma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2014(09): 514-532. [21] Laura Cutillas-Barreiro. Lithological and land-use based assessment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soils surrounding a cement plant in SW Europe[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6(03): 179-190. [22] 卿华. 水泥厂废气非正常排放的大气环境影响研究[J]. 建材发展导向, 2016(20): 62-63. [23] 赵文凯. 浅论水泥厂建设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J]. 环境保护科学, 2009(01): 124-125. [24] Maria C. Mirabelli, Steve Wing. Proximity to pulp and paper mills and wheezing symptoms among adolescents in North Carolina[J]. Environmental Reasearch, 2006(02): 76-80. [25] 刘耀东. 造纸厂水气污染现状分析[J]. 能源与环境工程, 2015(11): 79-80. [26] 蒋满元, 唐玉斌. 垃圾填埋的生态环境问题及治理途径[J]. 城市问题, 2006(07): 76-80. [27] Joaquim Rovira, Marta Schuhmacher. Concentrations of metals and PCDD/Fs and human health risks in the vicinity of a hazardous waste landfill: A follow-up study[J]. Huma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2015(10): 519-531. [28] Marinella Palmiotto, Elena Fattore, Viviana Paiano, Giorgio Celeste, Andrea Colombo, Enrico Davoli. Influence of a municipal solid waste landfill i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oxicological risk and odor nuisance effects[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14(03): 16-24. 29] 赵勇胜, 洪梅, 董军. 城市垃圾填埋场地下环境污染及控制对策[J].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 2007(07) : 136-141. [30] 朱晓玲. 环境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J]. 法制博览, 2014(02): 66. [31] Ali Ardeshiri, Mahyar Ardeshiri, Mohammad Radfar, Omid Hamidian Shormasty. The values and benefits of environmental elements on housing rents[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6(02): 67-78. [32] C. Y. Jim, Wendy Y. Chen. Impacts of urban environmental elements on residential housing prices in Guangzhou[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6(03): 422-434. [33] Patrick Bayer, Nathaniel Keohane, Christopher Timmins. Migration and hedonic valuation: The case of air quality[J].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9(01): 1-14. [34] Corey Lang. The dynamics of house price responsiveness and locational sorting: Evidence from air quality change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5(03): 71-82. [35] 周春晓. 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考量及其治理[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5(01): 128-132. [36] Janet Currie, Lucas Davis, Michael Greenstone, Reed Walker.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and Housing Values: Evidence from 1,600 Toxic Plant Openings and Closing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02): 678-709. [37] Arthur Katossky. The impact of hazardous industrial facilities on housing prices: A comparison of parametric and semiparametric hedonic price model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4(09): 93-107. [38] Brid Gleeson Hanna. House values, incomes,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J].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7(05): 100-112. [39] MICHAEL GREENSTONE, JUSTIN GALLAGHER. DOES HAZARDOUS WASTE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HOUSING MARKET AND THE SUPERFUND PROGRAM[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02): 951-1003. [40] 陈佛保, 郝前进. 环境市政设施的邻避效应研究[J]. 城市规划, 2013(08): 72-77. [41] 郑思齐, 刘洪玉. 市场比较法中因素调整过程的改进[C]. 中国房地产估价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3: 153-158. [42] 吴璟, 郑思齐, 刘洪玉. 编制住房价格指数的特征价格法细解[J]. 统计与决策, 2007(24): 16-18. [43] KENNETH Y. CHAY, MICHAEL GREENSTONE. THE IMPACT OF AIR POLLUTION ON INFANT MORTALITY: EVIDENCE FROM GEOGRAPHIC VARIATION IN POLLUTION SHOCKS INDUCED BY A RECESS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08): 1123-1167. [44] Siqi Zheng, Jing Cao, Matthew E. Kahn, Cong Sun. Real Estate Valuation and Cross-Boundary Air Pollution Externaliti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J].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4(03): 398-414. [45] Siqi Zheng, Matthew E. Kahn, Hongyu Liu. Towards a system of open cities in China: Home prices, FDI flows and air quality in 35 major citie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9(10): 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