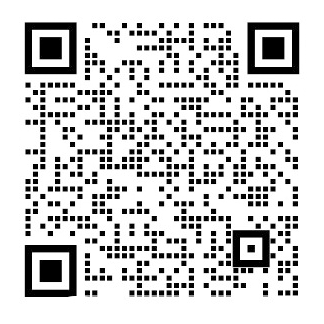从“三礼”看现代婚俗对传统婚俗的继承与发展文献综述
——以石浦地区为例
摘要:婚礼作为人生大事,古往今来,对其进行论述之人不胜枚举。而“三礼”,作为叙述先秦时期的仪礼和官制的典籍,是研究婚礼者必读之书目。今,搜集与“三礼”、婚俗礼仪及现代婚俗与传统婚俗比较研究的相关文献,对其分析归纳,形成文献综述。
关键词:婚俗; 三礼; 继承与发展;文献综述
一、关于婚姻词义及相关内容的研究
- 关于婚姻词义的研究
在研究婚俗之前,势必要先研究婚姻一词的含义。而古往今来,诸多学者对于婚姻一词的定义并无明确的一致性。“婚姻”,古人又写作“昏姻”,是由“婚”与“姻”组成的。婚姻一词的词义也与两者的词义密切相关。《尔雅》和许慎的《说文解字》皆认为“婚”指妇家,即妻族,“姻”指夫家,即夫族。其中,《尔雅》还认为“婚”和“姻”也可单单指女方和男方的父亲。而《白虎通》则持不同意见,其认为“婚”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婚嫁礼;一是指丈夫。“姻”指妻子。这两种解释看似矛盾,但其实不然。陈顾远在其《中国婚姻史》中引用了孔颖达的话来解释这种矛盾。孔颖达认为对于夫妻双方父母及家族而言,“婚”指女方的父亲或者妻族,“姻”指男方的父亲或夫族,而对于夫妻双方而言,“婚”指丈夫,“姻”指妻子。这两者含义的不明确常常会导致问题理解的偏差,如对《我行其野》的主人公的考证便涉及到对“姻”的理解。张琴在考证《我行其野》中“我”为弃妇还是弃夫的过程中,通过考证“求尔新特”的“特”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认为这首诗的主人公“我”应为弃夫。如此一来,问题便来了。那么诗句中的“不惟旧姻”中“姻”该作何解释?根据上述对“姻”的讨论可知,这里的“姻”只有丈夫的父亲、夫族和妻子的解释,显然在此种情况下,妻子意识不可能了,如此一来,“姻”便只能指丈夫的父亲或夫族。而张琴虽并没有对“姻”做出直接解释,但从其对所引用的朱熹的评论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张琴将“姻”解释为了丈夫,而这显然是不对的。无独有偶,另一位作者尚永亮为了确定《我行其野》的诗歌主题,对“言就尔居”者的身份进行了考证。他提出了两种观点,一是“言就尔居”者指的是与此婚姻有关系的亲属,并用朱熹和严虞惇加以佐证,在这种观点下,“姻”解释为“姻亲”。二是“言就尔居”者指的是丈夫。其第二种观点的解释有些混乱,一方面,尚永亮承认“姻”指妻子或夫家,另一方却又将“姻”解释为姻缘,亦是不对的。除此之外,马瑞辰也在“姻”字的理解上出现过偏差,他认为“姻”指的是妻子。这些错误的观点都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至此,“婚”与“姻”的定义已经很明确了,那么“婚姻”的意思也就出来了。陈顾远认为“婚姻”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嫁娶之礼,一是指夫妻双方的互称,一是指姻亲关系。
- 关于礼仪内容的研究
《仪礼》记嫁娶之礼有六,分别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对这六礼进行阐述解释和揭示礼仪的象征意义的著述很多。古代的有郑玄的“三礼”注疏,由班固编辑的《白虎通》,还有一些学者在注释其他书籍中对相关方面进行的阐释,如毛亨在注《诗经》的过程中,对涉及到婚姻礼仪方面的问题也进行了阐释。这些研究对后世对后世研究“三礼”中的婚姻礼仪内容具有很大的价值。近现代的也不少,有将近全部介绍的,如彭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一书,从婚礼、婚姻之义、议婚和定亲、亲迎、成婚、拜见舅故、古代婚礼的几个特色等方面有重点地介绍了相关内容,因介绍的方面较多,所以各部分的内容并无多大深入,多是蜻蜓点水,点到即止,内容浅显,通俗易懂。又如铁静的《从“三礼”看中国古代社会的婚俗》一文,该文主要介绍了女子笄例取字、婚礼仪式和妇学三个方面。在婚礼仪式方面,又具体讲了纳采、见面礼雁、纳征和事舅故。铁静在描述这些仪礼的同时,对这些仪式背后的文化意义进行了阐释,但铁静的阐释以揭露女性的社会地位为主,其思想内容多为对女性的同情,较为片面。也有取婚姻礼仪局部内容进行详细深入介绍的,如对婚龄的研究,何婷立在《试论周代婚龄及其影响》一文中,罗列了关于先秦时期婚龄的四种讨论:一是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二是男三十娶,女二十嫁是对于平民而言,贵族不限;三是男三十娶,女二十嫁是上限,过后男女结合不限;四是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可以提前婚龄。何婷立通过引用考古数据和文献相关史实记载,认为周代男女的婚龄应为男子普遍在二十上下,女子在十五上下,而所谓的三十与二十则是男女嫁娶的上限,也就是说男过三十,女过二十后便可自由结合,而不受礼法的约束。而国家在特殊情况下,亦可提前婚龄。因其应用考古数据和史实记载,因此其推论较为可信。赵会莉在《lt;诗经gt;中周代婚俗探微探》一文中也对婚龄进行了研究,其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推测当时男性婚龄一般在20至30岁,女性在15至23岁。这种推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主观性较强,缺乏说服力。而陈顾远对此持不同意见,其认为,在周代,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是规定,而那些早婚则是特殊例外。也有对称呼上进行研究的,如郑春苗的《舅姑甥侄称谓与中国古代婚俗》。郑春苗在文中提出,“舅故”一词在古时有两层含义:一是丈夫对妻子父母的称呼,一是妻子对丈夫父母的称呼。也就是说,在古时,夫妻双方对双方父母的称呼并无差别。郑春苗指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母系社会族外婚制的产物,或者说是“ 普那路亚家庭” 社会的产物。到了父系社会,这种称呼仍然被保留,但为了适应当时的婚姻关系,在彼此的称呼上做了些改变,如丈夫称呼妻子的父母由原先的“舅故”改为“外舅故”,这也是父系社会男性在婚姻中地位上升的反映。
- 关于婚姻礼仪功能的研究
在大多关于婚姻礼仪的研究停留在阐发解释、揭示象征意义和考证的现状下,焦杰在《附远厚别 防止乱族 强调成妇》一文中,通过对议婚地点、妇女婚前要教于公室、亲迎、共牢与说缨及见舅姑和舅姑飨妇这些礼仪细节的阐释,从社会性别学的视角探讨婚姻的实质与妇女思想的研究使人耳目一新。在对婚姻实质的认识上,焦杰认为婚姻不仅仅是男女个人之间的人生大事,更是关系家族存亡的大事。家族之间通过男女双方婚姻的建立而建立联系,成为彼此的外援,增强家族实力。从这一意义上看,婚姻实际上是一场家族之间的交易,是家族之间建立盟约的“媒介”。这就好比在现代社会,双方要进行合作,为了保证合作的有效开展,双方在合作之前会签订一个协议。而婚姻就好比这个协议,使双方合作有了稳定的基础。焦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女性是双方“建立友好关系的媒介”。但在我看来,在此种意义上,女性更像是个抵押物,作用就好比人质。我们都知道,两国交战后,有时战败国为了向战胜国表臣服的诚心,会向战胜国输送人质。当然,有时战胜国为了防止战败国反扑,也会主动要求战败国提交一个人质。这个人质并非随便选定的,他必然是在战败国中有一定地位的,多是战败国的子嗣。唯有至亲之人,才能使战胜国安心。当然,婚姻中的女性要比人质好,因为双方在建立婚约的时候,是平等的,是谋求双方合作的,大多并不存在着一方臣服另一方的境遇。在妇女观上,焦杰通过对士昏礼仪式的研究,认为在先秦人的观念里,未出嫁的女性是家族内乱、乱伦的隐患,而女子的出嫁是消除隐患的措施。而女子出嫁前要在公室受教也是为了防止已缔结婚约的女子在婚前被染指。不过与前面提到的女子为家族内乱隐患不同的是,前者要以防同族间乱伦为主,而后者以防被异族染指为主。因为在先秦,虽有男女大防的禁忌,但那多是针对同族人而言,对于异性外族,男女大防并不是很严格。为了证明这一点,焦杰还例举了《诗经》中的婚恋诗为证。而若女子在婚前被染指了,那么对于家族来说,便是灾难。焦杰还指出,在先秦时代,女性在人们的观念里,是暂居在母家的寄居者,而夫家才是她们真正的家,因此,女子出嫁也可用“归”来表示。而从母家归到夫家,需要通过亲迎、共牢与说缨等仪式来完成。焦杰认为,虽男女婚姻的存在是为了两姓之好,但真正在努力维护两姓之好的只有婚姻双方中的女性。他认为士昏礼中的诸多礼仪并没有对男性做出相关的要求和规定,而妇女则被诸多的道德礼仪所规范。这也形成了我国传统的妇女思想。焦杰的观点在诸多研究士昏礼的文献中,很是新颖。他从士昏礼细节出发,研究士昏礼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学性别观,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阐释了士昏礼,为我们研究士昏礼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其研究也是对婚姻礼仪功能的研究。从题目《附远厚别 防止乱族 强调成妇》便可看出。这三个词便是婚礼所起到的作用。